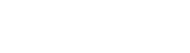广东客家与瑶族、畲族先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迁入粤地山区,这3个民系皆善于制作蓝靛以染色,蓝色是畲族、瑶族和客家服饰的主要颜色
关于瑶族使用植物染料染制衣物的记录很早就有,如汉代《后汉书·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织绩木皮,染以草实。”[6]乳源瑶族的《龙凤照批》又载:“后代以采,木朽柴滥,山土之荒,垅头垅尾,开挖田坵,栽蓝靛种姜点豆杂项,光彩尽行打落,免粮无税,客贩通行。”由此可知,瑶族先民在汉以前就已经学会使用植物染料染制衣物,而且古代瑶族人民普遍种植蓝草,蓝靛就是主要的植物染料。另外,瑶族妇女常在布料上刺绣几何图案样式,或在蓝染布料上通过蜡染和针线折染等工艺制成蓝底白纹的靛染花布,瑶族蜡染制作方法在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有详细记载:“猺人以蓝染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镕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猺人若也。”[7]
畲族长期以来是“大杂居、小聚集”的人口分布格局,使不同聚集地的民族在生活方式和衣着服饰等方面展现出不同的面貌。畲族曾被称为“菁客”,与瑶族、客家一样,皆善制作蓝靛染色,自明代以来,畲族人就在山上搭棚种植蓝草。杂居于粤地的畲族、瑶族和客家人皆住山区深处,世代农耕,为了方便农作,客家妇女与畲、瑶两族的女子一样皆不缠足,在服饰色彩上也主要选择蓝、黑等耐脏、耐晒、不易脱色、久经水洗的颜色,这对常年劳作的畲族、瑶族、客家人来说,是一个实用价值较高的选择。
3 广东畲族、瑶族、客家蓝染工艺对比分析
广东畲族和瑶族的蓝染工艺多样,如素染、蓝印花布等。除花布外,蓝靛素染在畲族和瑶族服饰中的应用也不在少数。墩头村民钟爱素染,在墩头村中并未发现有印染花布的特例,基于此,本研究就三者的素染工艺进行对比分析,试图找到其中的关联与差异(表1)。
表1 河源市墩头村客家、瑶族与畲族植物染料对比
续表1
《天工开物》记载了5种凡蓝,即菘蓝、蓼蓝、马蓝、吴蓝、苋蓝,皆可成淀[8]。通过表1的对比可知,植物染料(蓝靛)是用于蓝染的关键,由不同的蓝草发酵而成,不同种类的蓝靛可染出绿、碧、青等颜色,而这些蓝草的种植自然与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如广东墩头村的客家以种植马蓝为主[5],广东瑶族则使用蓼蓝,畲族蓝染工艺的选材却以蓼蓝辅以土茯苓为主。
蓝草被收割、清洗干净后便可用于制作蓝靛,这是蓝染工艺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制成合格的蓝靛膏,就无法进行染色。如墩头客家村民在浸泡蓝草前常先搅碎蓝草,可加快蓝草腐烂的速度,因此,墩头客家的蓝草发酵时间短于畲族和瑶族的蓝草发酵时间(表2)。蓝草发酵时间除了受人为加工影响外,还受季节和温度的影响,以上因素对蓝草腐烂与蓝靛素融出速度起到直接作用。蓝草发酵后,墩头客家、瑶族与畲族在捞腐叶、搅拌、沉靛和取靛泥的方法上多有相似之处。
表2 墩头村客家、瑶族与畲族蓝靛膏的制作工序对比
蓝靛的制作过程具有喜旱畏潮的特点,因为岭南地区春季湿度较高,所以每年只有在夏、冬、秋3个季节可以制作发酵。另外,蓝靛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石灰粉的比例,石灰粉的用量直接影响发酵的效果。如果石灰粉过量,蓝靛会呈现出淡灰色,染布颜色就不鲜亮;如果石灰粉过少,蓝靛则呈深蓝色,染出布的颜色就会偏青,且难以固色。
制作好的蓝淀膏不能直接染色,还需要经过还原过程生成可溶性的隐色体,这个过程称为建蓝,而建蓝又由建缸和养缸两个环节组成。在建蓝工序上,畲族、瑶族与客家无异,即将备好的蓝靛膏溶于水后与草木灰水搅拌均匀,便可倒入稀释后的白酒搅拌近3 min,当天需多次搅拌使其充分接触空气进行氧化。在草木灰水的调配方法上,三者有不同的讲究。瑶族人配制草木灰水的方式是在缸的上端制作一个铺有稻草的竹编筛子,在稻草上洒上水湿润草木灰,让经过草木灰过滤的水滴入缸内,以此方式往蓝靛膏内加入草木灰水。墩头村草木灰水的制作同样需要过滤,还需要进行加温处理,要先在草木灰中加水搅拌均匀并加温20 min后静置,待水温变为常温后,过滤到无杂质的状态,便可将草木灰水倒入缸中。
建缸完成后,需经过7~10天的养缸环节。养缸是为了保持缸内蓝靛分子的稳定性,需要染布时便可使用,染完布匹后,还需要继续养缸。墩头客家和瑶族、畲族的养缸方法大有不同。瑶族妇女在建缸完成后,每天用竹竿或木棒搅拌染液一次,直至数日后水呈现黄色为止。墩头村村民的养缸方法更有“晨灰、晚酒”的讲究,即清晨在染缸中加入草木灰水搅拌,傍晚加入米酒进行搅拌,早晚各搅拌3次,数日后待水呈现黄色则基本完成(表3)。
表3 墩头村客家、瑶族与畲族准备染液工序对比
建蓝环节完成后便可染布,一般情况下,布匹在染色前还需要进行脱浆处理(表4)。通过表4的对比可知,客家、瑶族与畲族都是使用温水搓洗布匹,将布匹中的浆洗去,这一步骤是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脱浆白布浸水后,将平展的染布正面朝下放入染缸,为了让染布充分接触染色素,需轻轻晃动染布。对于这一染布手法,三者并无太大差异,但每次浸泡的时间有较大差别。浸泡足时的布匹被捞起后会发生氧化,染布颜色由黄转蓝直至稳定不变为止,该步骤重复多次,直到达到预期的蓝色纯度和深度为止。
表4 墩头村客家、瑶族与畲族染布工序对比
客家人与瑶族、畲族由于久居粤地且长期处于杂居的状态,三者的蓝靛素染工艺在某些程度上呈现出逐渐融合的趋势。经过上文对河源市墩头村客家、瑶族和畲族蓝染技艺的对比,发现三者的蓝染工艺流程明显趋同,只是个别环节有所差异。如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中记载的明代畲族制作靛蓝染料的方法与如今广东畲族的制靛方法大不相同:“凌巨桶中,再越宿乃出其枝梗,纳灰疾搅之,泡涌微白,久之渐青。泡尽靛花与灰俱降,乃澄蓄之而泻出其水,则淀可滤而染矣。”[9]该方法是将蓝草在桶中浸泡后取出枝和梗,在桶中混入枝梗和石灰,快速搅拌至泛起微白的泡沫,静置一定时间,待颜色渐深,泡沫消失,蓝靛与石灰沉入桶底,上层水逐渐变清,再将蓝靛上层的废水排出,蓝靛经过过滤后便可进行染色。然而,明代畲族的制靛方法属于碱性水解法,只适用于菘蓝植物,对含有靛甙的蓼蓝并不奏效[10]。由此可知,明代广东畲族的制靛与当今的选材和染色方法有明显差异,与如今畲族使用的蓼蓝制靛工艺有所不同,或许与畲族、客家以及瑶族的蓝染工艺的交融有很大关系。
4 结语
河源市墩头村客家、瑶族和畲族蓝染工艺的工序不会脱离采叶、制靛、建蓝和染布的基本流程,但在一些环节上又有各自的特点,尤其表现在建蓝环节。古时蓝染技艺的传承多为手口相传,少有史料记录,能保存到现在的相关史料更是寥寥无几。因此,目前河源市墩头村客家、瑶族和畲族蓝染技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献资料非常有限,很难对其蓝染技艺进行纵向研究,期待有专家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钟文典.广东客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李筱文.五彩斑斓:广东瑶绣[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
[4]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5]李银广,陈建宏,朱彦,等.“墩头蓝”蓝靛制作与蓝染工艺考辩[J].装饰,2022(5):130-132.
[6](南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宋)周去非.岭外代答[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8.
[8](明)宋应星.天工开物[M].潘吉星,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01.
[10]闫晶.畲族服饰文化变迁与传承[D].无锡:江南大学,2019.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blue dyeing process of Hakka,She and Yao Nationality in Guangdong
Peng Min, Li Yingua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Hakka, Yao and She Nationality ancestors in Guangdong moved to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Guangdong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se three ethnic groups are good at making indigo for dyeing, blue is the main color of She and Yao Nationality and Hakka costumes.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separate research on the blue dyeing skills of these three ethnic groups, but there are no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se three ethnic groups are closely related in living habits and cultural beliefs through relevant documents. On this basis, it furth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blue dyeing skills of Hakka, Yao and She Nationality in Guangdong, and finds that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of the three are obviously similar, but they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ay of some links, especially in the link of blue building, which further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gdong Hakka and Yao and She Nationality is close in cultural life.
Key wordsblue dyeing; Duntou village; Hakka; Yao Nationality; She N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TS193
文献标志码:A
投稿日期:2022-04-25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科规划项目“岭南人文传统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以‘墩头蓝’传统染缬文化与文创开发为中心”(2020GZGJ199)
作者简介:彭敏(1998— ),女,广东河源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教育。
通信简介:李银广(1983— ),男,河南濮阳人,副教授,艺术理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后,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工艺美术史、美术教育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