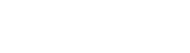二二八事件
軍事部署
主条目:二二八事件中的軍事部署
1947年3月,國民革命軍整編第二十一師士兵進駐臺南市
二二八事件最直接的加害是軍隊與憲兵鎮壓殘殺民眾[258]。在駐軍調往中國後,臺灣與澎湖群島兵力至少15,000人至20,000人,包括憲兵第四團、基隆要塞司令部、高雄要塞司令部、馬公要塞司令部等[259]。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的柯遠芬是僅次於陳儀的第二號人物,一開始便認為幕後有共產黨煽動「叛亂」 ,提出高度自治、獨立、託管等主張是意欲顛覆政府[260]。柯遠芬以陰謀論認定處理委員會的活動,派遣人員滲透、分化,並在事件擴大後嚴懲[261]。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利用紳士階級,勸請蔣渭川出面安撫民眾、斡旋糾紛,藉此分化處理委員會內部意見[262]。
在事件初期,陳儀積極請兵與部署,採地方司令指揮軍人、憲兵和警察維持治安的軍事狀態[263]。3月4日,經基隆地區、新竹地區、南部地區的軍事部署,提升為防衛司令備應「急變戰事」狀態[264]。其後政府展開一連串鎮壓與肅清,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首先全面鎮壓,基隆市、臺北市等北部地區繼而鎮壓市民,並發布戒嚴令與大逮捕[265]。國民政府派遣的整編第二十一師分別登陸基隆港和高雄港後,主要任務是以強勢武力掃蕩桃園鎮至嘉義市及東部地區的反抗勢力,其後主導採取連坐法的清鄉逮捕,師長劉雨卿並任由部隊在各地槍殺、報復民眾[266]。
在援軍抵達後,警備總司令部主導捕殺臺灣精英與民眾的行動,利用機會敲詐勒索,例如林本源家族的林宗賢因賄賂才倖存[267]。張慕陶的憲兵隊在戒嚴期間亦積極參與逮捕民眾,狂拘濫捕造成不少弊端[268]。海軍第三基地司令黃緒虞誇大危情、請求海軍總司令部增防軍艦,並將臺籍海軍技術員集中管制[269]。經蔣中正下令,海軍總司令部增派太康艦、太平艦、中海艦、美頌艦、美樂艦等船艦增防,在臺灣的中程艦、中權艦於左營港、基隆港、馬公港三地巡航[270]。3月19日,伏波艦在烏坵鄉被輪船招商局的海閩輪撞沉,100多名官兵喪生[269]。
整個綏靖計劃在中部和南部地區曾遭遇民間短暫的武裝反抗,如二七部隊、嘉義民兵和雲林民兵發動的戰役,其他各地幾無戰鬥便如期完成[271]。但中華民國建國後戰亂不已,且中國抗日戰爭影響軍隊教育甚大,導致軍政制度和風紀未能嚴整清明,鎮壓與綏靖過程充滿違法濫權、空白授權與無法狀態,並有大量弊端產生[272]。雖然蔣中正並未明令鎮壓或具體處置方式,且曾言申紀律、禁止施加報復,部分駐軍指揮官也力予矯正,但未能有效防範和約束不法弊端發生,造成許多無辜性命喪生;其中最常見的有公報私仇、因糾紛遭到殺害,或是為了奪取、勒索財物而殺人[273]。
情報機構
國防部保密局情報透露王添灯已經遭到密裁,而陳復志亦已經槍斃
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參軍處軍務局是當時情報樞紐,下有軍事統計局改組的國防部保密局、中央統計局及憲兵司令部(後二者與前者對立),在臺灣各地部署調查員與線人,監視民眾動向、傳遞情報[274]。軍事統計局最早來到臺灣,以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室掩護部署網絡,情報蒐集的深度與廣度較深;其後縮編為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林頂立擔任站長,並在事件中擴張[275]。中央統計局所屬的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調查室欠缺偵緝職權,須結合憲兵勢力偕同工作[276]。憲兵司令部憲兵第四團兼具情蒐體系與行動能力,所屬特高組被賦予執行行動偵緝、特殊任務職權[277]。
3月3日,柯遠芬召集陳達元、張慕陶、林頂立等情報機構負責人,要求偵查幕後策動分子的動態,以備「平亂」之用[278]。在事件中,保密局滲透各地處理委員會、青年團與自衛隊、《臺灣新生報》報社、中部自治青年同盟本部等,並強勢擴張勢力,新增協助緝辦的外延單位[279]。其中保密局指揮許德輝組成忠義服務隊,表面號召青年學生維持治安交通,實則編列流氓製造混亂擴大事端,事後反而歸罪學生[280]。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調查室同樣提供名冊、試圖分化閩客、吸收流氓人士、滲透處理委員會、協助搜捕調查行動,並以清鄉「肅奸」為名進行報復鬥爭[281]。
軍人、警察和線人還反間策劃製造紛爭、加工武裝騷亂、設置陷阱誘殺,如圓山附近「暴民」攻擊海軍辦事處等機關、楊亮功遭遇狙擊事件等,並成為軍隊鎮壓的理由[282]。各系統情報機構人員還分別密電中央政府,捏造、喧染和誤導情勢嚴重程度,凸顯陳儀完全失去掌握能力打擊其威信,並推卸無法協助維持局勢穩定的責任,及請求援兵武力鎮壓的理由[283]。情報機構人員誇大動盪情形與暴動人數、強調共產黨黨員達萬人、凸顯中國人傷亡程度,更指稱參與者是懷有叛國、獨立、奪權之重要陰謀行為,國民政府因這類情報報告而影響派兵鎮壓的決定[284]。
情報機構人員在臺灣社會緊密佈線、監視輿情,羅織罪名製造各種「暴徒」名冊及「參與事件人調查」,作為列冊緝辦、行動偵緝、逮捕槍斃的證據[285]。情報機構藉由不同管道調查、吸收流氓、操控大眾,不少線人或臥底提供情報資訊、告密構陷他人,擴大事件傷害[286]。政府還以連坐法威脅交出「惡人」,在獎勵密告與指認流氓的政策下,告密者與構陷者造成許多個案[287]。當中亦有地方流氓提供情資、詐欺恐嚇案例,但告密者的身份大多隱密不公開[288]。在事件過後,政府還強化山地行政及管控政策,國防部保密局派遣特務針對原住民族精英進行監控工作[289]。
縣市政府
1947年3月7日,陳儀同意處理委員會提出的縣市長民選要求,但其後相關人士均遭到槍斃
戰後臺灣縣市行政首長與警政首長因貪污無能而未獲民間好評,且僅有臺北市市長游彌堅、新竹縣縣長劉啟光、高雄縣縣長謝東閔三位半山人士;部分日治時期的地方政治精英則是參選縣市參議員[290]。在事件紛亂期間,各地處理理委員會為首的「談判交涉-和平解決」路線,與青年學生為主的「收繳武器-武力解決」路線結合[291]。因應混亂衝突,地方領袖精英、民意代表、紳士階級與民眾和政府交涉,提出改革政治要求,並組成處理委員會、治安維持會、自衛隊等[292]。部分組織接收槍械、接管機關、維護秩序,甚至將武裝路線視為談判「籌碼」,以拓展最大利益[293]。
在二二八事件中,部分縣市長與處理委員會協調合作,不得民心者棄職躲避逃亡,或激烈對抗、請兵鎮壓,對地方衝擊不一[294]。臺北市市長游彌堅、臺北縣縣長陸桂祥、臺中市市長黃克立、臺中縣縣長宋增榘、臺南縣縣長袁國欽將縣政交由處理委員會維持[295]。彰化市市長王一麐、高雄市市長黃仲圖、臺東縣縣長謝真等配合處理委員會[296]。反之,新竹市市長郭紹宗、嘉義市市長孫志俊、屏東市市長龔履端等與處理委員會對抗[297]。基隆市市長石延漢、新竹縣縣長朱文伯、臺南市市長卓高煊、高雄縣縣長黃達平、花蓮縣縣長張文成、澎湖縣縣長傅緯武等則與地方駐軍配合[298]。
在多個縣市政府無法行使職權下,以縣市參議會民意代表為主的處理委員會及地方分會,負責維持秩序、協商,並提出處置對策與改革方案[299]。3月7日,處理委員會提出「長官公署改組臺灣省政府」、「各廳長平等起用臺灣人」、「縣市長在7月1日直接選舉」等要求,陳儀表示接受,並允諾可以「改選不稱職縣市長」[300]。部分縣市處理委員會呼應陳儀指示,推舉3位縣市長候選人呈請陳儀圈定,部分縣市則支持現任縣市長[301]。例如臺南市推選黃百祿、侯全成、湯德章為市長候選人,花蓮縣推選張七郎、馬有岳、賴耿松為縣長候選人,部分候選人後來遭逮捕槍斃[302]。
在二二八事件後,黃克立、朱文伯、郭紹宗、孫俊志、陸桂祥、石延漢請辭職務並立即照准,游彌堅、宋增榘、王一麐、卓高煊、黃仲圖、龔履端、黃達平、袁國欽、張文成、謝真、傅緯武等續任或調任他職,大幅影響地方政務推動;不過當時縣市層級在統治結構中為次要角色,賞罰標準並不明確[303]。同時,部分縣市參議員名列事件要犯、甚至喪生,其他參議員轉而支持陳儀、協助善後處理;但因對政治感到失望與冷漠,後續出席人數銳減、議事工作相對消極低落[304]。此外,部分基層公務員、軍人、憲兵和警察人員在事件中藉機勒索敲詐,但部分警政人員則因事件喪生[305]。
其他機關
1947年3月16日,臺灣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的遺體被發現棄置在南港橋下
長官公署全力推動「去日本化」、「中國化」政策,將中國制度延伸至臺灣施政,特別對日治時期以近代法律思潮培養的臺灣法律專業人才存有疑慮[306]。在二二八事件中,有高達20%的臺灣司法官、律師等司法界精英及司法人員死亡、失蹤,或被逮捕、拘禁、通緝等,其中臺灣高等法院推事吳鴻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王育霖、律師李瑞漢、李瑞峰、林連宗、陳金能、林桂端、湯德章等人喪生[307]。因為事件衝擊、語言文化等環境因素,許多臺灣法律精英從司法體系轉業,甚至離開臺灣;留在法界的人必須適應新的司法文化,甚至棄守部分法治理念[308]。
部分外省籍司法人員、法律精英在事件中遭到毆打或損失財物,引發離職出走潮,忌諱採用本地人才的政府降低司法人員任用標準、擴大引進外省人才的彈性,出現牽親引信現象[309]。其中20多名不具任用資格者進入臺灣司法體系,而違反《法院組織法》等人事法規的權宜性任命援用到1950年代初期[309]。該措施加速臺灣司法體制與文化中國化的速度,在地法律人才遭到邊緣化,且族群溝通不良[309]。同時在法官終身職的制度保障下,拉低法院司法人員的素質,長期影響臺灣司法案件的品質;而處理二二八事件相關案件的非法程序與習慣也影響往後的審判文化[309]。
隨著國共內戰爆發,中國共產黨藉由學生運動妨礙中國國民黨,臺灣的學生運動與抗爭四起[310]。在二二八事件中,臺北市學生傳播消息、號告抗爭,原先對長官公署及教育政策的不滿擴大,大量青年學生成為抗爭主力,協助維持治安、組織青年團體、提出改革要求,甚至積極參與武裝攻擊與接收行動,包括國立臺灣大學、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臺灣省立農學院、臺灣省立工學院、臺灣省立嘉義中學、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等[311]。這導致各級學校陷入停頓,部分學校教師、行政人員、青年學生因為事件喪生、被捕、失蹤,部分青年學生組織亦遭到報復[312]。
二二八事件後,基於各地青年學生以「盲從附和」者居多,政府宣布寬大處理、既往不咎原則,進行學校復課及整肅學風工作,提供救恤與補救措施[313]。同時展開一系列整頓學校的處置措施,包括查封關閉延平學院等學校,視情節懲戒師生等[314]。政府還將事件歸因於「日本奴化教育遺毒」,重新檢視「中國化」政策,訂定各式思想和觀念上的再教育訓育規則,藉此增強對中國的認同和向心力[315]。這樣由上而下、由外而內規範各級學校及學生行為,嚴格規範原先自由開放的校園內外秩序,往後教育、文化更長期受到黨化教育和戒嚴影響[316]。
半山人士
1967年10月5日,前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舊屬在臺北國賓大飯店聚餐,其中有多名半山人士參與
半山人士是指出身臺灣、在臺灣有一段生長經歷,在日治時期前往中國大陸,加入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工作,因而對中國的政治文化有所涉獵者[317]。雖然半山人士應扮演中國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中介,但大多只急切呼籲政府「收復臺灣」[318]。儘管臺灣調查委員會囊括半山人士,實際運作以陳儀的江浙同鄉與其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時的班底為主[319]。部分半山人士曾向國民政府提出接管臺灣的注意事項,例如臺灣調查委員會的半山人士曾建議接管臺灣應「多用臺灣人」、以臺灣人為行政主體,但是政府對於半山人士的建言甚為輕忽,甚至予以否定[320]。
由於半山人士具有特殊的「中國經驗」,並非長期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且資訊受限的臺灣在地人所能相比,因此國民政府希望在接管臺灣之後,能夠借用這批人士治理臺灣[321]。在政治派系鬥爭的背景下,半山人士在戰爭結束後紛紛回到臺灣,並出任政壇的要職,形成一股「半山集團」[322]。但儘管陳儀希望借重半山人士改善長官公署與臺灣民眾的關係,然而部份半山人士實際上成為接管過程中的受益者,與臺灣本土精英也存在著權力、利益的競逐關係,結果半山人士在戰後初期反而並未成功扮演中介角色,甚至成為官民之間的障礙[323]。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臺灣民間社會對於任職政府機關的半山人士有許多負面的批評,認為他們「出賣」臺灣人[324]。陳儀曾運用臺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副議長李萬居、秘書長連震東、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林忠等半山人士居間斡旋,試圖恢復秩序、維持治安,但多基於陳儀立場協助平息抗爭,而非以臺灣民眾立場向陳儀爭取權益[325]。部分半山人士受到政府重用、實際參與鎮壓行動,又以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新竹縣縣長劉啟光、新竹地區防衛司令兼新竹縣縣長蘇紹文、長官公署警務處處長王民寧、臺中區防衛司令黃國書等人為典型[325]。
對於清鄉工作,臺灣民間流傳是半山人士協助提供「黑名單」,警備總司令部才能羅列「暴動首謀」清單緝捕,以致各地的精英遭捕殺,而半山人士經常被視為是二二八事件實際的受惠者[326]。不過雙方存在附屬關係,政府並未完全信賴半山人士、或給予決策地位,使其只能扮演外省籍接收官員的附庸角色[327]。同時只有忠誠且順從的半山人士才會受到重用,半山人士在二二八事件中也可能因為其立場、批判時政而遭到槍斃,例如曾任《人民導報》社長的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等[328]。
社會團體
1947年3月8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發表告同胞書
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中國國民黨各勢力進入臺灣,臺灣人捲入黨國不分的政治派系鬥爭[329]。在訓政體制之下,一般民眾只能組織以職業團體為主的人民團體,中央俱樂部派的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便企圖操控政治建設協會等社會團體[330]。在臺灣省黨部協助下,原先基於臺灣民眾黨精英成立的臺灣民眾協會,改組成具合法地位的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在各地設置分會[331]。但其積極提出去殖民地化、實施地方選舉等臺灣人自治理念,使李翼中和陳儀感到不滿[331]。同時期還有臺灣省憲政協進會、臺灣重建協會等團體[332]。
最初政府調查報告將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與擴大歸咎於一些社會團體,特別是共產黨、三民主義青年團與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等[333]。在舊臺灣共產黨勢力爭執主導權下,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地下黨黨員在各地吸收不滿百人,僅在臺灣各地從事新聞宣傳、武裝學生等介入工作,無法承擔策劃、煽動與主導事件[334]。三民主義青年團並非一般社會團體,是訓政體制下與黨部平行的特殊組織,當時有許多臺灣左翼份子加入、批判政府腐化貪污[335]。許多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或精英參與各地抗爭,但屬個別的行動、而非組織行動,並因此喪生或被捕[336]。
遭到利用後被迫解散的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是受害最深的社會團體[337]。陳儀等人曾經請託領導人蔣渭川出面安撫民眾,其後卻以公開徵調臺籍日本兵出面維持社會治安、背叛國家為理由,下令解散[338]。政治建設協會在鎮壓過程中傷亡慘重,多名幹部被捕遇害或失蹤,王萬得、潘欽信等四處躲藏或逃亡海外[339]。警備總司令部還解散多個「非法組織」,半山人士組織的臺灣省憲政協進會趁勢崛起,在事件後發起臺灣新文化運動委員會,多數成員日後更成為政治新貴[340]。另外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在二二八事件之中亦有許多行動[341]。
由各地民意代表、紳士階級、青年學生組成的處理委員會等組織是這場紛爭的主角,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意基礎[342]。各類民意代表、縣市參議員、政府官員等所占比例由北而南、由西而東遞減,越基層的分會和支會比例越低[343]。處理委員會大多認為事件是對政治腐敗的不滿,整合民意、溝通交涉、撥借米糧、協調民生、維持治安、制止衝突,一度取代各地政府功能,並謹慎提出政治改革要求[344]。在事件後,處理委員會主要成員被以不同名目清算,包括列入名冊、發布通緝、自首自新、逮捕監禁、徒刑感訓、槍斃私刑等,縣市層級又比縣市以下層級嚴峻[345]。
新聞媒體
主条目:二二八事件對新聞媒體的影響
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對於事件發展的相關報導
政府報告曾經點名「輿論不當之影響」是二二八事件原因之一,認為媒體言論激發民眾反對政府的情緒[346]。當時在公、民營報社激烈競爭下,新聞媒體工作者對政府施政有諸多批評與揭露,形成輿論影響[347]。但除了經濟因素打擊經營外,政府藉由媒體宣傳、新聞政策排擠,展開嚴密的管制,新聞媒體只能「照實報導」[348]。同時政府禁止報紙日文版、取締報刊雜誌左翼言論活動,情報機構也對印刷媒體展開監控,並在後來以此指控罪狀[349]。但即便是照實報導,每天報紙上的消息大多是軍人開槍、警察亂紀、官員貪污、物價飆漲等,也因此遭受懲處[350]。
3月8日,隨著軍隊開抵臺灣,為了打壓、報復和肅清異議者,政府逮捕或殺害不少報社主要負責人、主管與新聞記者,震懾言論思想自由[351]。《民報》社長林茂生、《臺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和日文版主編吳金鍊、《人民導報》前後任社長宋斐如和王添灯、《大明報》總編輯艾璐生、《臺灣新生報》臺中分社記者陳安南、嘉義分社主任蘇憲章和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等人遭到殺害,《民報》總編輯許乃昌和總主筆陳旺成則被通緝而逃亡[352]。3月13日,警備總司令部發布命令,查封《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等多家主要的民營報社[353]。
在訓政體制下,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負有蒐集情報的職責,設有臺北分社將採訪的臺灣新聞傳回南京總社,葉明勳為負責人[354]。不過其電文報導完全基於陳儀政府和軍方立場,不斷出現外省人遭到毆打、甚至曲解真相的錯誤訊息,忽視臺灣民眾的意見和社會騷亂的實情,甚至是建議國民政府派兵鎮壓[355]。由於中央通訊社是國民政府瞭解臺灣政情的重要管道,其傳達的訊息對於蔣中正的派兵決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356]。各地無線電廣播電臺遭民眾佔領也被視為是事件擴大的原因,政府強化掌控廣播電臺,管制電報、電話通訊網[357]。
另外,政府還查扣各種「反動刊物」,並嚴格禁止左傾言論[358]。最終有16家官民營報社遭查封或停刊,或發行人、記者被逮捕殺害;政府和情報機構除了管制新聞業,並與中國大陸媒體工作者直接控制或重組報刊雜誌、廣播等新聞媒體主導權[359]。在1949年發布《臺灣省戒嚴令》、1950年確立動員戡亂體制後,制定諸多限制新聞自由的管制法令,臺灣精英失去發言權[360]。政府更以「戴紅帽」方式封鎖訊息,將事件原因歸諸共產黨陰謀,並讓新聞媒體避談二二八事件[361]。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後,相關新聞管制隨之鬆綁、廢除,媒體環境逐漸趨向正常[362]。